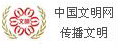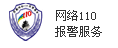至宋明无论性即理(理学)还是心即理(心学)皆心性之学,而佛、道二教同样大讲心性,而心性之学为三教共同之理论基础,故三教归一之说实依于此心性本体论。
(《涅槃经集解》卷51,见《大正藏》第37册,第533页中)宝亮在讨论涅槃之体时,提到了体相和用,即涅槃之体相没有规定性,这一点与虚空相同,但与虚空不同之处是涅槃之体相还有其用,即常乐我。因为关于体义的思考仅仅停留在体一义异而没有到达相即的高度,所以最终被体-德体-用范畴所取代。

在这种概念框架中,体意味着法身,而德则意味着般若和解脱。体用义的说法,从形式上看,似乎是把体用和体义概念糅合在一起,新创造出的一组概念。第五云:二谛以中道为体。体用作为思维工具,比之体义更具有普适性。体者圆极妙有之本也,德者波若解脱之流也。
[13]张文良,2019年:《南朝成実宗における二諦説——杏雨書屋蔵·羽271〈不知題仏経義記〉の二諦義を中心に》,载《東アジア仏教学術論集7》,東洋大学東洋学研究所。(《敦煌秘笈影片册四》,第160页,羽271号写本,第8号图版,第9-12行)德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概念,在佛教语境中往往表达主体的属性和功用,与用的概念联系在一起使用。关于朱子改亲民为新民是否适宜,当时就有门生提出这个问题,直接问朱子:程子之改亲为新,何所据?子之从之,又何所考而必然耶?且以己意轻改经文,恐非传疑之义,奈何?2朱子则回答说:若无所考而辙改之,则诚若吾子之讥矣。
一、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的原因和依据《大学章句》是对《大学》的守正创新。由此观之,朱子更为看重身教的示范作用,而不是简单的言传。5 赵法生:《〈大学〉亲民与新民辨说》,《中国哲学史》2011年第1期。朱子说:若论了得时,只消‘明明德一句便了,不用下面许多。
(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4页)也即,明德是本体,明明德是内圣之事,新民是末,是外王之事。首先,来看新民之所以可能的第一个因素。

从这个角度讲,虽然上之人和下之人存在阶级立场的对立和具体目标的差异,但在新民问题上有着求同存异的可能。(《朱子语类》卷十六,第390页)由此可知,朱子是赞同新民必本于在我之自新的说法的。(《大学或问》,第509-510页)朱子的回答不仅阐明了改亲民为新民的依据及其可靠性,也间接表达了改动的原因。就学者修己治人而言,朱子通过诠释新民展现了大学之道、为学之法,不仅为人们明明德、新民、止于至善指明了方向,还指出了具体实现方式和现实路径,这对于君子得闻大道之要和小人得蒙至治之泽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。
还具有方法论意义,同时指明了新民的两个向度:一是返本开新,二是借鉴外来。如果能将此二者结合起来,必能赋予新民以新时代意蕴,激活其历史生命力。人本身固有的东西,只要肯下功夫、只管做去,便可以实现自新新民。按照朱子的说法,新者,革其旧之谓也,言既自明其明德,又当推以及人,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。
在谈论礼让为国时,朱子说:自己礼让有以感之,故民亦如此兴起然后有所之,即意向性(intentionality),亦即意志。

上文孟子谈到孔子惧,作《春秋》的恐惧情绪、我亦欲正人心的救世情怀、其所根据的是非之心的本真情感,都凸显出孟子诠释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,那就是情感。(二)缘情说诗上述缘情知言在经典诠释中的体现,就是孟子的缘情说诗——总是从情感出发去诠释经典。
《礼记》确认,惧与欲属于七情:何谓人情?喜怒哀惧爱恶欲,七者弗学而能。显然,毛亨的说法既符合心理规律,也符合孔孟的情感诠释思想。岂好辩哉?予不得已也。[108] 陈嘉映:《谈谈阐释学中的几个常用概念》,《哲学研究》2020年第4期,第11‒19页。[24]《孟子注疏·尽心上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767页。颂同诵,朱熹集注颂,‘诵通[94]。
此篇记载武王伐纣,血流漂杵,极为血腥,故孟子不尽信。[51] 朱熹:《孟子集注·万章上》,《四书章句集注》,第306页。
(二)经典诠释的目的:正人心与邪相对的是正。[41]《孟子注疏·告子下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756页。
孔子不选择晋之《乘》、楚之《梼杌》,而选择鲁之《春秋》,是有深刻原因的:一方面,晋国、楚国都是春秋五霸之一,正是孔子和孟子所批判的专制霸道。孩提之童,无不知爱其亲者。
综上所述,看起来是人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,实质上却是生活在创造经典、诠释经典:生活在通过诠释而创造经典。这里,认知者和被认知者都牵连在同一阐释过程之中。其兄关弓而射之,则己垂涕泣而道之,无他,戚之也。[11]《尚书正义·周书·武成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185页。
有学者说: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,其真切地逼近《诗》篇之‘志,也只是作为自己的‘支援意识,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‘集中意识——所谓‘意也。所不虑而知者,其良知也。
学者指出:这种价值判断首先是诠释者之‘意,如果作者也有相通的心性,那么诠释者之‘意与作者之志就能够达成一致,两人心同理同、莫逆于心。这看起来类似于伽达默尔所谓‘Hermeneutik的工作总是这样从一个世界到另一个世界的转换,从神的世界转换到人的世界,从一个陌生的世界转换到另一个自己语言的世界[102]。
[50]《孟子注疏·题辞解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663页。[71] 李凯:《孟子的诠释方法及其应用》(上),《儒学全球论坛(2006)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》,2006年4月,第375‒388页。
[⑥]《孟子注疏·公孙丑上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686页。如赵岐注:在三皇之世为上,在五帝之世为次,在三王之世为下。[78]显然,孟子认为:经典诠释就是一个由详返约的论辩过程。黄玉顺:《生活儒学导论》,《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——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》,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,第38‒40页。
这种意义不是现成地取来的,而是孔子赋予的,此即托文赋义,即对意义的重新认识和重新构造[83]。[28] 许慎:《说文解字·力部》,辨属于宋代新附字,中华书局1963年版,第293页。
[77]这里所谓详说之说,即指辩说。[88]《论语注疏·八佾》,《十三经注疏》,第2467页。
最早对孔子《春秋》大义进行揭示的是《左传》:《春秋》之称,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尽而不污,惩恶而劝善[85]。事史是说关于春秋五霸当中的齐桓公、晋文公的事实、史实。